
洪燭《遙遠(yuǎn)的八大胡同》一文惹爭議。附錄蔣晗玉《也談八大胡同》。
《遙遠(yuǎn)的八大胡同》■ 洪燭
談?wù)摷伺潜容^敏感的話題。但在舊時(shí)代,妓女也包括在叁教九流的范圍之內(nèi),與販夫走卒無異。因而我輩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時(shí),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。
雖然唐宋的詩人(譬如贏得青樓薄幸名的杜牧,
對(duì)妓女的記載一般只能見之于野史之中。恐怕要算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,較早介紹了北京地區(qū)(時(shí)稱元大都)妓女的規(guī)模與狀況。馬可·波羅說,新都城內(nèi)和舊都(金中都)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約二萬五千人,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個(gè)特設(shè)的官吏監(jiān)督,而這些官吏又服從總管的指揮。給人的感覺是,元大都對(duì)妓女也實(shí)行半軍事化管理,而督察大員則相當(dāng)于百夫長或千夫長,行之有效地統(tǒng)率著天子腳下的紅粉軍團(tuán)。妓女甚至進(jìn)入了這個(gè)歐亞大帝國的外事(外交)領(lǐng)域:“每當(dāng)外國專使來到大都,如果他們負(fù)有與大汗利益相關(guān)的任務(wù),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。為了用最優(yōu)等的禮貌款待他們,大汗特令總管給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個(gè)高等妓女,并且每次一換。派人管理她們的目的就在于此。”妓女的“覺悟”好像也挺高,“都認(rèn)為這樣的差事是自己對(duì)大汗應(yīng)盡的一種義務(wù),因此不收任何報(bào)酬”。不知馬可·波羅統(tǒng)計(jì)的妓女?dāng)?shù)目是否有夸張的成分?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冊(cè)登記的暗娼?而“賣淫婦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內(nèi)營業(yè)的,她們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營生……無數(shù)商人和其他旅客為京都所吸引,不斷地往來,所以這樣多的娼妓并沒有供過于求”。看來那是一個(gè)“性解放”的時(shí)代。不過在當(dāng)時(shí),除了元大都之外,全世界恐怕沒有第二座城市能養(yǎng)得起如此龐大的妓女隊(duì)伍。元大都的“客流量”真是太可觀了。
明朝的北京,紅燈區(qū)又是什么樣的呢?現(xiàn)只聽說,導(dǎo)致吳叁桂沖冠一怒的紅顏陳圓圓,就是“叁陪女”出身:“姓陳名沅,為太原故家女,善詩畫,工琴曲,遭亂被擄,淪為玉峰歌伎,自樹幟樂籍而后,艷名大著。凡買笑征歌之客,都喚她做沅姬。身價(jià)既高,凡侍一宴須五金,為度一曲者亦如之。走馬王孫,墜鞭公子,趨之若鶩,大有車馬盈門之勢。即詞人墨客,凡以詩詞題贈(zèng)沅姬的,亦更仆難數(shù)。”后來,崇禎皇帝駕下西宮,國丈田畹,以千金購之,將其包養(yǎng)起來。再后來,吳大將軍去田府串門,一見圓圓,驚為天人,愛得要死要活……
明清兩朝,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,妻妾成群。紫禁城儼然已成最大的“紅燈區(qū)”。大紅燈籠高高掛,只不過叁千粉黛,都是為一個(gè)人服務(wù)的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來說,宮女無辜(雖然也會(huì)爭風(fēng)吃醋“搶生意”),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貪婪最無恥的“嫖客”。明帝大多短命,想是太沈溺于女色的緣故。而清帝中,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,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,其中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。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,讓小太監(jiān)扮作仆人,頻頻光顧八大胡同,跟上了癮似的。結(jié)果染上梅毒,十八歲暴卒。既誤國,又害了自己。
此外,晚清還出過個(gè)賽金花。賽金花絕對(duì)屬于“另類”。她生長于煙花巷陌,遇見大狀元洪鈞,就從良了。雖然只是妾,她卻以夫人身份隨洪鈞出使德、俄、荷、奧四國,算是出過遠(yuǎn)門,見識(shí)了外面的花花世界(甚至拜晤過維多利亞女王與威廉皇帝),很出風(fēng)頭的。自海外歸來,因洪鈞早逝,家里斷炊了,就重操舊業(yè)。陳宗蕃《燕都叢考》記載:“自石頭胡同而西曰陜西巷,光緒庚子時(shí),名妓賽金花張艷幟于是。”以昔狀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門賣笑,本來就適宜作為花邊新聞炒作,賽金花的“生意”一定很不錯(cuò),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。偏偏賽金花天生是盞不省油的燈,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:八國聯(lián)軍侵占北京期間,她與德帥瓦德西鬧了場滿城風(fēng)雨的“跨國之戀”……真不知她怎么想的。
說起老北京的妓院,人們首先會(huì)想到八大胡同。所謂八大胡同,并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,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,位于前門外大柵欄附近,因妓館密集而成一大銷金窟。《京都勝跡》一書引用過當(dāng)時(shí)的一首打油詩曰:“八大胡同自古名,陜西百順石頭城(陜西巷口的百順胡同、石頭胡同)。韓家潭畔弦歌雜(韓家潭),王廣斜街燈火明(王廣福斜街)。萬佛寺前車輻輳(萬佛寺系一小橫巷,西通陜西巷,東通石頭胡同),二條營外路縱橫(大外廊營、小外廊營)。貂裘豪客知多少,簇簇胭脂坡上行(胭脂胡同)。”
民國后,袁世凱擔(dān)任臨時(shí)大總統(tǒng),為八大胡同火上澆油。他出手很“大方”,花高價(jià)收買參、眾兩院八百名議員(號(hào)稱八百羅漢),每人月薪八百塊現(xiàn)大洋。而國會(huì)的會(huì)址位于宣武門外象來街(今新華社)。“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,南城一帶產(chǎn)生了畸形的繁榮,許多商界、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信用咔管理津津有味地談起‘八百羅漢’鬧京城時(shí)的盛況……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。‘八百羅漢’酒足飯飽之后,當(dāng)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游。位于前門、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(qū),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‘客滿’的牌子。”這段文字,見之于方彪著《北京簡史》。唉,八大胡同,竟然“載入史冊(cè)”了。
八大胡同曾是賽金花“重張艷幟”之處,但畢竟出了小鳳仙那樣真正的義妓。袁世凱復(fù)辟稱帝期間,滇軍首領(lǐng)蔡鍔身陷虎穴,為擺脫監(jiān)控,假裝醉生夢死,放蕩不羈于八大胡同,因而結(jié)識(shí)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鳳仙。小鳳仙膽識(shí)過人,掩護(hù)臥薪嘗膽的蔡將軍躲避了盜國大賊的迫害。“一九一六年,一個(gè)叫蔡松坡(蔡鍔)的人,在云南舉行了倒袁起義,打碎了袁世凱的迷夢。這位蔡鍔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圖書館。面對(duì)蔡鍔的起義,袁世凱籌劃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黃粱般破滅了……”(林語堂語)蔡鍔為我國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馬功勞,其中似應(yīng)有小鳳仙的一份,多虧她助了一臂之力。古人常說英雄救美人,可這回卻是淪落風(fēng)塵的美人救落難的英雄。
根據(jù)《燕都舊事》一書引用的資料:“民國六年(1917年),北平有妓院叁百九十一家,妓女叁千五百人;民國七年(1918年),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,妓女叁千八百八十人。民國六七年間,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。公私相加,妓女就在萬人之上了。民國十六年(1927年),首都南遷,北平不如過去繁榮,妓院、妓女的數(shù)字也隨之下降。民國十八年(1929年),北京頭等妓院有四十五家,妓女叁百二十八人;二等妓院(茶室)有六十家,妓女五百二十八人;叁等妓院(下處)一百九十家,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;四等妓院(小下處)叁十四家,妓女叁百零一人。以上共計(jì)妓院叁百二十九家,妓女叁千零五十二人。但實(shí)際上暗娼的數(shù)字很大,真正妓女的數(shù)字比這大得多。”據(jù)說妓院的房間很矮小擁擠,跟鴿子籠似的,只能放下一張床及一桌一椅。那里面收容著煙花女子們扭曲的人生。
葉祖孚先生曾重新參觀了從前妓院舊址。他去了朱芳胡同九號(hào),那里原來是家二等妓院,叫聚寶茶室,門框上面“聚寶茶室”四字猶存。“聽說在一次房管局修繕房屋過程中,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憤怒地要求鏟掉門口這四個(gè)字,他們不愿意這些象征恥辱的痕跡仍舊保存著。”朱家胡同四十五號(hào),原先的妓院叫“臨春樓”,門框上刻有“二等茶室”的字樣;里面的住戶,抬頭低頭都能看見,估計(jì)同樣很不是滋味。“這里樓下五間房,樓上也是五間房,每間房約九平方米,原先樓上樓下都是七間房,每間房只有六平方米,后來改成五間,略大了些,但仍是鴿子籠似的……”妓院分叁六九等,其中的頭等者,硬件設(shè)施要高檔一些,甚至很豪華,可以想見其門前車馬喧囂的情景。而百順胡同,就是精裝修的頭等妓院之集中點(diǎn),專為上流社會(huì)提供服務(wù)的。譬如四十九號(hào),是個(gè)四面環(huán)樓的院落(屬于另類的四合院),“每面四間房,樓上共十六間,樓下也是十六間,每間房均十平方米大。有個(gè)樓梯通到樓上,樓梯還結(jié)實(shí),樓上還有雕花的欄桿。看了這個(gè)頭等妓院,可以想象從前這里妓女倚門賣笑,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樣子,從這里散發(fā)出來的污濁空氣腐蝕著整個(gè)北京城。”頭等妓院除了經(jīng)營“老本行”,額外還提供餐飲游樂,堪稱全方位的服務(wù)。韓家潭二十七號(hào),即叫做“清吟小班”的地方,“門口上面有個(gè)名叫李鐘豫的人題了‘慶元春’叁字,是這家妓院的名字。這里院子比較寬暢,只有南北兩面有兩層樓房,每面都是樓上四間,樓下四間,兩面共十六間房,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,每間約有十平方米。這是富人們的銷金窟,除了可以嫖妓外,吃得也不錯(cuò),經(jīng)過修理的樓梯上還釘著一塊‘本莊寄售南腿’的木牌,證明從前這里的飲食水平。”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。只是,聞風(fēng)而至的公子王孫,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,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,在乎美人之玉腿。
值得一提的是,這花枝招展的韓家潭(今名韓家胡同),曾是閑散文人李漁的隱居之地。“他生于明清之際,進(jìn)北京似在入清以后,請(qǐng)張南垣為他在韓家潭壘石蓄水,仍以他在金陵的別墅‘芥子園’為名,題楹聯(lián)曰:十載藤花樹,叁春芥子園。”芥子園,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。放蕩不羈的李笠翁,即使挾妓醉飲,也不會(huì)怎么臉紅的。他老人家并不在乎與八大胡同的秦樓楚館為芳鄰,不在乎后人說閑話。
前一段時(shí)間,有好事者,倡議修繕八大胡同妓院遺址,作為旅游景點(diǎn),吸引中外觀光客,哪怕是進(jìn)行一番“憶苦思甜”的教育,也有積極意義。此言一出,在報(bào)端立即招致眾人反對(duì)。有人說:老北京的風(fēng)俗,不能靠八大胡同來表現(xiàn),有趣味的地方多呢,天橋、大柵欄、琉璃廠等等,夠玩的了。有人說:讓八大胡同重新曝光,不過是為了滿足某些現(xiàn)代人對(duì)妓女生活的好奇心與窺視欲,會(huì)產(chǎn)生毒害作用的。凡此種種,都恨不得將八大胡同夷為平地,最好是索性將其從我國人的記憶里抹去。
抹,是抹不去的。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歷史階段的產(chǎn)物。至于是否有必要列為景點(diǎn)隆重推出,確實(shí)夠讓人為難的。懷古乎?懷舊乎?八大胡同,似乎跟巴黎的紅磨坊、紐約的紅燈區(qū)還是有區(qū)別的。東、西方的道德觀念,也還是有區(qū)別的。所以,本地雖然一直向外來游客推薦“胡同游”(坐在老式的人力車上,體驗(yàn)一番“胡同竄子”的感覺),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,即使不能算禁地,也屬于被(刻意)遺忘的角落。
談?wù)摷伺蝗缭谡務(wù)摵樗瞳F。八大胡同,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紅燈區(qū),仿佛是人類囚禁、奴役自身的“動(dòng)物園”,或者說,都展覽著人性向獸性演變的復(fù)雜過程,令后世之觀者惆悵不已、五味俱全。是的,我們無意間目擊了人類心靈中曾有過的陰暗面。華美的肉體與丑陋的靈魂,形成鮮明的對(duì)比。
《燕都往事談》一書,在原則乃至語氣上把握得很省⒑苷,雖涉及了一些煙云往事(或煙花往事),但特意在代序中強(qiáng)調(diào):“舊北京也有它的陰暗面:公開和不公開的妓院,形形色色的賭博,以及算卦相面、坑蒙拐騙……充斥著這座古城的底層,散發(fā)著臭氣,毒害著人民。紙醉金迷的‘八大胡同’是罪惡的淵藪,使古城失色。北京解放以后,這些垃圾堆被鐵掃帚掃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本書記下這些資料,目的在于讓后人知道舊社會(huì)曾有這樣的渣滓,以便提高警惕,千萬不能讓沈渣泛起。”
讀老照片,能對(duì)清末的妓女有更為直觀的印象。我發(fā)現(xiàn),當(dāng)時(shí)有兩類女性頗愛照相的。其一是宮廷女性(以慈禧太后為代表),其二是煙花女子。前者是因?yàn)榕c洋人接觸的機(jī)會(huì)多,難免忍不住好奇心,攝影留念。后者也同樣如此,只不過場合不同罷了。外國使節(jié)或傳教士,在紫禁城和頤和園里,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,是很累的,生怕破壞了禮儀。于是,業(yè)余時(shí)間,就去泡八大胡同,放心大膽地見識(shí)神秘的東方女性。飲酒作樂之余,難免技癢,順便掏出照相機(jī)來,摁一摁快門。在我國的民間女子中,很難有誰能像妓女這么大方,經(jīng)得起陌生的藍(lán)眼睛的挑逗與注視。于是,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“攝影愛好者”們,終于在八大胡同深處尋找到最稱心如意的模特兒。
賽金花各個(gè)時(shí)期的玉照,堪稱是當(dāng)時(shí)最“上鏡”的我國女性了,拍照時(shí)比慈禧太后要放松,況且也更年輕。挺會(huì)擺姿式、做表情的。如果不加以說明,你會(huì)以為畫中人是某大家閨秀。
更多的則是一些無名女郎,穿著形形色色的旗袍,或中式棉襖,在畫棟雕梁間搔首弄姿。客觀地說,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較樸素(有些尚未擺脫村姑的稚氣),比同時(shí)期上海灘的摩登女郎要顯得土氣一些。她們雖然碰巧進(jìn)入“洋鏡頭”了,但估計(jì)還沒使用過巴黎香水、倫敦口紅。
有一幅照片,內(nèi)容是這樣的:兩位俄國大兵(肯定是八國聯(lián)軍的),各自正摟著一個(gè)強(qiáng)作笑顏的妓女(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強(qiáng)作出來的),圍坐在八仙桌邊,高舉酒杯合影。只需看一眼,你就會(huì)明白,所謂的“鐵蹄”指的是什么。當(dāng)時(shí),連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顫栗,更何況八大胡同呢?這一回,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照相機(jī)了,還有口徑更大的槍炮。想一想那一時(shí)期的我國,命運(yùn)的悲慘,似乎并不比茍且偷生的妓女強(qiáng)到哪里。需要同時(shí)面對(duì)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,我國簡直連招架之力都沒有。
舊我國,對(duì)于垂涎叁尺的西方列強(qiáng)來說,就是可以自由進(jìn)出、肆意妄為的八大胡同。他們到這塊古老而豐腴的土地上來,是為了尋芳探寶的,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蹂躪其自尊。他們并不是腰纏萬貫來消費(fèi)的,而是借助堅(jiān)船利炮來掠奪的。
從那妓院的照片里,可以看到一個(gè)時(shí)代的影子,一個(gè)無比屈辱因而無比漫長的瞬間。表情尷尬的女性,她們承擔(dān)著的其實(shí)是雙重的恥辱(從肉體到靈魂),因?yàn)樗齻儾粌H是飽受欺凌的妓女,同時(shí)又是毫無尊嚴(yán)的亡國奴。而此時(shí),我國的男人們都到哪里去了?為什么拋棄了自己柔弱的姐妹?據(jù)了解,當(dāng)時(shí)我國的天字第一號(hào)“男子漢”——皇帝本人,已一溜煙地逃出紫禁城,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難去了。唉,光緒,臨出逃前不僅無法搭救心愛的珍妃(被慈禧太后下令投進(jìn)井里),而且更顧不上照料首都的婦女們(包括社會(huì)底層的妓女),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即將身陷水深火熱之中……
難怪有騷客借用古代郛國夫人的詩句,來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:“盡無一人是男兒!”
日本電影《望鄉(xiāng)》,通過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經(jīng)歷的滄桑巨痛,表現(xiàn)了一群“南洋姐”被祖國拋棄(甚至歸國后還受到歧視)的苦難生活。作為一個(gè)戰(zhàn)敗國,能以電影的方式對(duì)那一卑微的群體加以關(guān)注與追悼,恐怕需要一番“激烈的思想斗爭”才能做出決定的。
而我國人,不大可能為八大胡同(尤其是八國聯(lián)軍侵華期間的)拍一部電影的。正如他們?cè)谛睦砩习寻舜蠛懦诠袍E保護(hù)的范圍之外一樣。八大胡同,哪能算“文物”?哪能辟作旅游景點(diǎn)?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嗎?傳統(tǒng)的觀念是:家丑不可外揚(yáng),舊事(主要指負(fù)面的)不必重提。我國人,不大好意思(或沒有勇氣)直面慘痛的歷史與慘淡的人生,更談不上反思以及檢討了。他們常常選擇回避或遺忘來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尷尬與羞恥,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錯(cuò)誤。
痛定思痛,倒也不失為一種美德,或一種勇敢。逛北京城,無意間碰見八大胡同遺址,其實(shí)大可不必繞道而行。
也談八大胡同
蔣晗玉
今年第四期《書屋》有洪燭先生《遙遠(yuǎn)的八大胡同》一文,該文對(duì)八大胡同歷史有許多應(yīng)了解而未觸及處,“遙遠(yuǎn)”及開新眼界處不多。在下不恥學(xué)淺,就個(gè)人所知八大胡同相關(guān)資料作點(diǎn)補(bǔ)充。
一、八大胡同與男風(fēng)
同性戀現(xiàn)象是始終伴隨人類歷史的。我國有文字可考的同性戀現(xiàn)象,上自先秦。如《尚書·商書·伊訓(xùn)》載“叁風(fēng)十愆”中“亂風(fēng)”內(nèi)含的“四愆”便是比頑童;《周書》中作為俗語出現(xiàn)的“美男破老,美女破舌”;《戰(zhàn)國策·秦策一》講晉臣荀息獻(xiàn)美男計(jì)于宮之奇“乃遺之美男,教之惡宮之奇”。另外“泣角竊駕”、“余桃新袖”的典故和相關(guān)同性戀現(xiàn)象記載更豐富。再下至當(dāng)今,如言及“在我國約叁千九百萬至五千二百萬的同性戀人群”的李銀河《同性戀亞文化》所作的調(diào)查研究,說明該現(xiàn)象不容忽視。
而男性間出賣肉體,性交易的相公業(yè),以明清為盛,以優(yōu)伶為主要從業(yè)對(duì)象。魯迅《我國小說史略》中言:“明代雖有教坊,而禁士大夫涉足,亦不得狎妓,然獨(dú)未云禁招優(yōu)。達(dá)官名士以規(guī)避禁令,每呼伶人侑酒,使歌舞談笑;有文名者,又揄揚(yáng)贊嘆,往往如狂酲,其流行于是日盛。清初,伶人之焰始稍衰,后復(fù)熾,漸乃愈益猥劣,稱為‘像姑’流品比乎娼女矣。”
而相公業(yè)最發(fā)達(dá)集中的地方在哪里呢?——京城八大胡同。
洪燭文中有“所謂八大胡同,并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,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”之說,并舉那首將胡同細(xì)名包括在內(nèi)的詠八大胡同詩一首為證。然作為一個(gè)特定名詞,人們固然可以舉出八大胡同所包括的八條街巷名稱,但也不必過于拘泥,實(shí)際只要知其大致范圍即可。如《都門識(shí)小錄》中言“八大胡同又名十條胡同,以該處大小巷計(jì)之,有十條也”。可見胡同建筑、街巷、胡同名稱自明至清多有變遷,說法不一,作為一個(gè)區(qū)域名稱看待“八大胡同”似更好些。大致宣武門、正陽門外,大柵欄、煤市街以西,琉璃廠以南,虎坊橋以北,以韓家潭為首,附近十?dāng)?shù)條胡同范圍內(nèi)。
我們來看看作于道光八年的《金臺(tái)殘淚記》講述一個(gè)破敗了的“老斗”(同性戀嫖客)回顧昔日繁華的眷戀:“王桂官居粉坊街,又居果子巷。陳銀官嘗居?xùn)|草場。魏婉卿嘗居西珠市。今則盡在櫻桃斜街、胭脂胡同、玉皇廟、韓家潭、石頭胡同、豬毛胡同、李鐵拐斜街、李紗帽胡同、陜西巷、北順胡同、廣福斜街。每當(dāng)華月昭天,銀箏擁夜,家有愁春,巷無閑火,門外青驄嗚咽,正城頭畫角將闌矣。嘗有倦客,侵晨經(jīng)過此地,但聞鶯千燕萬,學(xué)語東風(fēng),不覺淚隨清歌并落。嗟乎!是銷魂之橋,迷香之洞邪?”〔1〕
再看:齊如山先生在《齊如山回憶錄》中所說:“私寓又名相公堂子。在光緒年間,這種私寓前后總有一百多處。光緒二十六年以前四五年中,就有五、六十家之多。韓家潭一帶沒有妓館,可以說都是私寓。”〔2〕 可見八大胡同在娼妓業(yè)繁盛之前,相公業(yè)占據(jù)了絕對(duì)的優(yōu)勢。相公堂(或稱下處、私寓)、相公(或稱像姑、私房、老板、兔子〔俗罵男孩“小兔崽子”便從這來,人多未知其惡毒也〕)、老斗(玩弄相公者,年長或稱干爹),這些合在一起,構(gòu)成了一個(gè)完整的買賣體系。
讓我們先看看相公堂的外景。《側(cè)帽余譚》載:“門外掛小牌,鏤金為字,曰某某堂,或署姓其下。門內(nèi)懸大門燈籠一,金烏西墜,絳蠟高燃,燈用明角,以別妓館。過其門者無須問訊,望而知為姝子之廬矣。”〔3〕 再進(jìn)入相公堂內(nèi)看看。寫于嘉慶十五年(1810年)的《聽春新詠》曾載:“小慶齡、叁慶部。色秀貌妍,音調(diào)體俊,寓居櫻桃斜街之貴和堂。”(櫻桃斜街與李鐵拐斜街、韓家潭、五道廟交匯)這貴和堂“座無俗客,地絕纖塵。玉軸牙簽,瑤琴錦瑟。或茶熟香清,或燈紅酒綠。盈盈入室,脈脈含情。花氣撩人,香風(fēng)扇坐。即見慣司空,總為惱亂。擬諸巧笑之章,當(dāng)嫌未盡”。《燕京雜記》:“優(yōu)童之居,擬于豪門貴宅。其廳事陳設(shè),光耀奪目,錦幕紗廚,瓊筵玉幾,周彝漢鼎,衣鏡壁鐘,半是豪貴所未有者。至寢室一區(qū),結(jié)翠凝珠,如臨春閣,如結(jié)綺樓,神仙至此當(dāng)跡矣。”
然后我們看看這堂寓下處的諸種活動(dòng)吧。《清稗類鈔》言之甚詳:
伶人所居曰下處,懸牌于門曰某某堂,并懸一燈。客入其門,門房之仆起而侍立,有所問,垂手低聲,厥狀至謹(jǐn)。俄而導(dǎo)客入,庭中之花木池石,室中之鼎彝書畫,皆陳列井井。至此者,俗念為之一清。 老斗飲于下處曰喝酒。酒可恣飲,無熱肴,陳于案者皆碟,所盛為水果、干果、糖食、冷葷之類。酒罷,啜雙弓米以充饑。光緒中葉,酒資當(dāng)十錢四十緡,賞資十八緡,凡五十八緡耳。其后銀價(jià)低,易以銀五兩。銀幣盛行,又易五金為七圓或八圓,數(shù)倍增矣,然猶有清益者。 老斗與伶相識(shí),若以數(shù)數(shù)叫條子矣,則必喝酒于其家。或?yàn)樵娨约o(jì)之。中四語云:“得意一聲拿紙片,傷心叁字點(diǎn)燈籠。資格深時(shí)鈔漸短,年光逼處興偏濃。”拿紙片者,老斗至下處,即書箋,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。點(diǎn)燈籠者,酒闌歸去時(shí)之情景也? 老斗之飯于下處也,曰擺飯。則肆筵設(shè)席,珍錯(cuò)雜陳,賢主嘉賓,即醉且飽。一席之費(fèi),輒數(shù)十金,更益以庖人、仆從之犒賞,殊為不貲。非富有多金者,雖屢為伶聽嬲,不一應(yīng)也。 老斗之豪者,遇伶生日,必?cái)[飯。主賓入門,伶之仆奉紅氍毹而出,伶即跪而叩首。是日,于席費(fèi)犒金外,必更以多金為伶壽。r座之客,且贈(zèng)賀儀,至少亦人各二金,伶亦向之叩首也。
二、八大胡同與戲劇
老北京伶界有句俗語:人不辭路,虎不辭山,唱戲的不離百順、韓家潭。可見八大胡同與戲劇,特別是京劇的形成發(fā)展的歷程有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。
洪燭先生文中談到李漁在韓家潭的芥子園時(shí)說,“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”。不肯定的“恐怕、可能”的措詞說明作者下意識(shí)到自己的武斷處吧。這里只說:八大胡同與戲劇界的關(guān)聞,文化遺跡之多已不是“惟一”了。
李漁憑跑江湖的家班實(shí)踐和《閑情偶記》的理論,以及大量的劇本創(chuàng)作,成就了其戲劇大家的歷史地位。他康熙初年寓居韓家潭,其宅有一頗幽默對(duì)聯(lián),“老驥伏櫪,流鶯比鄰”,只是這“流鶯”還真不好辨雌雄呢。 另孔子第六十四代孫,官至戶部主事、員外郎,住宣武門外時(shí)稱海波巷(今稱海北寺街)的戲劇大家,寫《桃花扇》的孔尚任亦是在八大胡同區(qū)域居住。康熙叁十九年(1700年)正月“人日”(初七),孔尚任邀集十八位文人墨士在家中聽伶人演唱《桃花扇》。他在《庚辰人日雪霽·岸堂試筆分韻》詩并序中興高采烈地描繪了這次雅集。說到《桃花扇》自要說起女主角妓女李香君了,孔尚任孔門子孫,儒學(xué)大家,士大夫之族,對(duì)最下層的妓女卻給予了不同尋常的歌頌。劇中批語云:“巾幗卓識(shí),獨(dú)立天壤”、“妓女倡正倫,真學(xué)校朝堂之羞也”、“壓倒須眉”、“男人齊拜倒矣”,這較之洪燭先生對(duì)賽金花的輕謾無識(shí)實(shí)要人文關(guān)懷,難能可貴得多。
洪先生只知賽金花在八大胡同張艷幟,卻不知她憑借流利德語游歷歐洲見識(shí),走出八大胡同直面八國聯(lián)軍司令瓦德西的勇氣,對(duì)其勸聯(lián)軍不要濫殺無辜,保護(hù)了不少
義和團(tuán)
拳民,保護(hù)了清宮建筑……試問當(dāng)時(shí)有幾個(gè)男兒做得到呢?
徽班進(jìn)京對(duì)京劇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。1790年清高宗弘歷為舉辦八旬大壽,命浙江鹽務(wù)大臣承辦皇會(huì)。閩督伍拉納命其子親率安徽二慶徽戲班進(jìn)京祝禧演出,便下榻八大胡同之韓家潭。此后四喜、春臺(tái)、和春等戲班相繼來京,分別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順胡同、陜西巷和李鐵拐斜街。四大徽班扎根在南城,扎根在戲園、戲樓集中的大柵欄和八大胡同。
八大胡同及其周圍至近代以來,其聚集的科班有:長春科班,國劇研究社(齊如山、梅蘭芳、余叔巖組織),富連成科班(梅蘭芳、周信芳、賈大元等數(shù)十人帶藝入科學(xué)戲的名班),斌慶社、小榮椿班、正樂社、榮春社、鳴春社、承華社(梅蘭芳組織)。
京劇名伶大都在八大胡同之韓家潭、百順胡同、石頭胡同、王廣福科街等胡同內(nèi)居住,現(xiàn)在宣武區(qū)保存了一批尚好的故居。比如梅蘭芳1894年生于李鐵拐斜街,1900年其家遷至百順胡同,后又遷至蘆草園街。其母逝后又搬到鞭子巷頭條……
京劇藝術(shù)生長在相公業(yè)日漸發(fā)達(dá)的八大胡同區(qū)域,加之明代戲班的男旦體制的確立,優(yōu)伶男旦與相公結(jié)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關(guān)系。操相公業(yè)的除歌童小唱、剃頭仔、曲藝檔子、頓子等,主要就是戲劇伶人。
讓我們來看看當(dāng)時(shí)的戲園內(nèi)男旦相公與老斗之間的丑行惡態(tài)吧。《夢華瑣簿》:“戲園分樓上、樓下。樓上最近臨戲臺(tái)者,左右各以屏風(fēng)隔為叁、四間,曰官座,豪客所聚集也。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,以其搴簾將入時(shí)便于擲心賣眼。”〔4〕另開戲之前,戲園有“站條子”(或稱“站臺(tái)”)的惡習(xí)。主要男旦扮好戲裝站立臺(tái)口讓“老斗”們品頭論足。一旦在臺(tái)上看到相識(shí)的老斗,他們就會(huì)眉眼傳情,作姿作態(tài),并且還會(huì)直接下臺(tái)前去侍候。當(dāng)時(shí)在演出安排上,流行由主要男旦演“壓軸兒”,之后的“大軸兒”(送客的大武戲)將散之際,男旦就好換裝完畢與老斗登車,去附近酒樓或下處“銷魂”去了。對(duì)同性戀現(xiàn)象描述很多的小說《品花寶鑒》第叁回對(duì)這些戲樓現(xiàn)象有入微的展示:
不多一回開了戲,重場戲是沒有什么好看的。望著那樓上,有一班像些京官模樣,背后站著許多跟班。又見戲房門口簾子里,有幾個(gè)小旦,露著雪白的半個(gè)臉兒,望著那一些起人笑,不一會(huì)就攢叁聚五的上去請(qǐng)安。遠(yuǎn)看那些小旦時(shí),也有斯文的,也有伶俐的,也有淘氣的,身上的衣裳,卻極華美:有海龍,有狐腿,有水獺,有紫貂,都是玉琢粉妝的腦袋,花嫣柳媚的神情,一會(huì)兒靠在人身邊,一會(huì)兒坐在人身旁,一會(huì)兒扶在人肩上,這些人說說笑笑,像是應(yīng)接不暇光景,聘才已經(jīng)看出了神。又見一個(gè)閑空雅座內(nèi),來了一個(gè)人,這個(gè)人好個(gè)高大身材,一個(gè)青黑的臉,穿著銀針海龍裘,氣概軒昂,威風(fēng)凜冽,年紀(jì)也不過叁十來歲,跟著叁四個(gè)家人,卻也穿得體面,自備了大錫茶壺、蓋碗、水煙袋等物,擺了一桌子,那人方才坐下。只見一群小旦,蜂擁而至,把這一個(gè)大官座也擠得滿滿的了……
正在看他們時(shí),覺得自己身旁又來了兩個(gè)人。回頭一看,一個(gè)是胖子,一個(gè)生得黑瘦,有了微須,身上也穿得華麗,都是叁十來歲年紀(jì),也有兩個(gè)小旦在跟著說閑話,小廝鋪上坐褥,一齊擠著坐下。……忽見那胖子扭轉(zhuǎn)的手來,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。那相公道:“你做什么,使這樣勁兒?”便側(cè)轉(zhuǎn)身向胖子坐了,一雙手搭在胖子肩上。那先坐的兩個(gè)相公,便跳將下去,摔著袖子走了。又聽得那胖子說道:“蓉官,怎么兩叁月不見你的影兒?你也總不進(jìn)城來瞧我,好個(gè)紅相公,我前日在四香堂等你半天,你竟不來,是什么緣故呢?”那蓉官臉上一紅,即一手拉著那胖子的手道:“叁老爺今日有氣。前日四香堂叫我,我本要來的,實(shí)在騰不出這個(gè)空兒,天也遲了,一進(jìn)城就出不得城,在你書房里住原很好,叁奶奶也很疼我,就聽不得青姨奶奶,罵小子,打丫頭,摔這樣,砸那樣,再和白姨奶奶打起架來,教你兩邊張羅不開。明兒早上,好曬我在書房里,你躲著不出來。”蓉官?zèng)]有說完,把那胖子笑得眼皮裹著眼睛,沒了縫,把蓉官嘴上一擰罵道:“好個(gè)貧嘴的小么兒,這是偶然的事情,哪里是常打架嗎?”聘才聽得這話,說得尖酸有趣,一面細(xì)看他的相貌,也十分可愛,年紀(jì)不過十五六歲。一個(gè)瓜子臉兒,秀眉橫黛,美目流波,兩腮露著酒凹,耳上穿著一雙小金環(huán),衣裳華美,香氣襲人…… 八大胡同區(qū)域戲樓茶園、酒樓飯莊、堂寓下處這種斗相麇至、打情罵俏、不堪入耳的場景當(dāng)年是處處可見。時(shí)人蔣只儕曾記:“八大胡同名稱最久,當(dāng)時(shí)皆相公下處,豪客輒于此取樂。庚子拳亂后,南妓麇集,相公失權(quán),于是八大胡同又為妓女所享有。”光、宣之際,北京妓業(yè)的興盛程度已經(jīng)超過相公業(yè),清亡,民國肇造,娼妓徹底勝過相公。這里必須提到一位著名的戲劇藝術(shù)家田際云,他于民國元年四月十五日遞呈于北京外城巡警總廳,請(qǐng)禁韓家潭一帶相公寓,以重人道。而他宣統(tǒng)叁年就擬上批呈,卻反被相公中有背景有財(cái)力的買通官府,反告他而使他被捕,關(guān)了百多天才放出。這也是我國相公業(yè)最后的掙扎了。這次田際云勝利了,總廳食剩并于同月二十日發(fā)布告示,文曰:
外城巡警總廳為出示嚴(yán)禁事:照得韓家潭、外廊營等處諸堂寓,往往有以戲?yàn)槊T良家幼子,飾其色相,授以聲歌。其初由墨客騷人偶作文會(huì)宴游之地,沿流既久,遂為納污藏垢之場。積習(xí)相仍,釀成一京師特別之風(fēng)俗,玷污全國,貽笑外邦。名曰“像姑”,實(shí)乖人道。須知改良社會(huì),戲曲之鼓吹有功;操業(yè)優(yōu)伶,于國民之資格無損。若必以媚人為生活,效私倡之行為,則人格之卑,乃達(dá)極點(diǎn)。現(xiàn)當(dāng)共和民國初立之際,舊染污俗,允宜咸與維新。本廳有整齊風(fēng)俗、保障人權(quán)之責(zé),不斷容此種頹風(fēng)尚現(xiàn)于首善國都之地。為此出示嚴(yán)禁,仰即痛改前非,各謀正業(yè),尊重完全之人格,同為高尚之國民。自示之后,如再陽奉陰違,典買幼齡子弟,私開堂寓者,國律具在,本廳不能為爾等寬也。切切特示,右諭通知。〔5〕
叁、洪燭所述八大胡同有關(guān)人事之異議
(一)“而清帝中,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,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,其中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。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,讓小太監(jiān)扮作仆人,頻頻光顧八大胡同,跟上了癮似的,結(jié)果染上梅毒,十八歲暴卒。既誤國,又害了自己。”同治于1861年8月其父咸豐死,旋繼位時(shí)五歲多,辛酉政變后決定自1862年改元,同治已六歲,至1874年亡,共十叁年,同治壽元應(yīng)為十九歲。同治是死于天花還是梅毒迄無定論,也許將來開陵驗(yàn)骨或驗(yàn)發(fā)會(huì)有結(jié)論吧。他是嫖妓染病而亡,還是狎優(yōu)、玩相公中毒也不好定論的。一是咸同時(shí)期八大胡同是相公的天下,時(shí)人以狎娼為不齒,以狎優(yōu)為名士風(fēng)流,這是有史料可查的。這里講更重要的一點(diǎn)是同治有同性戀活動(dòng)記載。如《梵天廬叢錄》卷二謂其與宮中太監(jiān)有染;《清代野記·詞臣導(dǎo)淫》曾載同治帝與翰林王慶其狎坐一榻共閱秘戲圖;《清稗類鈔·優(yōu)伶類·侯俊山顧盼自喜》言同治與名優(yōu)侯俊山關(guān)系為“穆宗殊嬖之”;《異辭錄》載:“同治末有某伶者,相傳曾為上所幸”。近人沃丘仲子費(fèi)君行簡所著《慈禧傳信錄》言“又有奄杜之錫者,狀若少女,帝幸之”。他又引用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中語“狎迎宦豎,遂爭導(dǎo)以嬉戲游宴”,“耽溺男寵,日漸羸瘠,未及再其,遂以不起。哀哉”!
帝王好男寵歷代有之,縱以上野史皆未可信,我們也不好只信洪先生的,哪怕他知道同治脫了龍袍換的是布衣。
(二)洪文講到賽金花時(shí)說“因洪鈞早逝,家里斷炊了,就重操舊業(yè)”。筆者記得賽金花傳記中,洪鈞死后(也不是什么早逝),其大老婆怕賽金花再入娼門分了不少銀子給她,何至斷炊?一個(gè)狀元郎,出使歐洲數(shù)國之重臣,死后妾會(huì)斷炊是不好想象的。洪文又言“賽金花的‘生意’一定很不錯(cuò),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。”不知其所指,只知有點(diǎn)語法錯(cuò)誤。另外要告訴洪先生的是賽金花是開妓院的,不是一個(gè)人操業(yè)的。
(叁)“唉,八大胡同,竟然‘載入史冊(cè)’了”,不知洪先生載入史冊(cè)為何要用引號(hào)引起來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都有佞幸列傳,鄧通、韓嫣、李延年這些為皇帝用口吮痛膿,被皇帝玩弄的同性戀者都可以載入正史,八大胡同上一上《北京簡史》應(yīng)毫不為過。
(四)洪文講八大胡同某妓院樓梯上釘著一塊“本莊寄售南腿”的木牌,“證明從前這里的飲食水平,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。只是聞風(fēng)而至的公子王孫,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,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,在乎美人之玉腿。”八大胡同的妓業(yè)是分檔次的,公子王孫都如洪先生所想那么猴急,那么“出污泥而不染的小鳳仙”也只能濁不堪言了。飲食是妓業(yè)中一項(xiàng)重要內(nèi)容,應(yīng)是常識(shí)。至于金華火腿不能證明八大胡同的飲食水平,也應(yīng)是常理,這塊牌的價(jià)值不在“火腿”而在“金華”上。清末十幾年妓業(yè)興盛的表現(xiàn),一是南班增多。南班妓者來自江南蘇浙一帶,與本京北妓相比,南妓娛客的手段要顯精致嫵媚。“妓寮向分南北兩幫。大抵南幫活潑而不免浮滑,北幫誠實(shí)而不免固執(zhí)。南幫儀態(tài)萬方,酬應(yīng)周至。若北幫則床第外無技能,偎抱外無酬酢”(《清稗類鈔·娼妓類·京師之妓》)由于南妓自身的長處,她們批量入京后自然大受歡迎。這一方面提高了北京妓業(yè)的招客能力,另外促使北妓去做一些改進(jìn),南北兩幫妓女合力對(duì)抗相公,后者便愈現(xiàn)頹敗之勢。而那一木牌就正反映了這一南妓北上的現(xiàn)象。另賽金花、鳳仙皆是南人哦。
(五)洪燭先生發(fā)現(xiàn)清末兩類女性愛照相。一是宮中女,二是妓女,而且攝影者他都想像全為外國人。清朝的我國人就開始拍電影了,德國的鐵甲艦也都可以讓我國人開到日本去激發(fā)他們加強(qiáng)海軍建設(shè)了。我國人玩相機(jī)、開相館應(yīng)還有這個(gè)可能,因?yàn)橛泻芏嗉伺恼掌窃谟胁季暗南囵^里拍的,其中應(yīng)有我國開辦的吧。鄧拓先生有一篇雜文叫《歡迎雜家》,廣博充分地占有資料是我們發(fā)議論的前提,在下也只是一個(gè)東抄西摘的“文抄公”而已。對(duì)于八大胡同的歷史存在,完全可以作多學(xué)科更深入的研究的,目前已有很多扎實(shí)的學(xué)人取得了不少成果,我們要學(xué)習(xí)他們的“耐煩”。
版權(quán)聲明--以上內(nèi)容與本站無關(guān),自行辨別真假,損失自負(fù)
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(diǎn),不代表本站立場與本站無關(guān)。如有侵權(quán)請(qǐng)及時(shí)聯(lián)系本站郵件 enofun@foxmail.com ,如未聯(lián)系本網(wǎng)所有損失自負(fù)!
本文系作者授權(quán)本網(wǎng)發(fā)表,未經(jīng)許可,不得轉(zhuǎn)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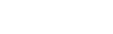



評(píng)論